在我国外语界,有一位著名学者,他就是戴镏龄先生。由于当今认识戴先生的人不多,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下这位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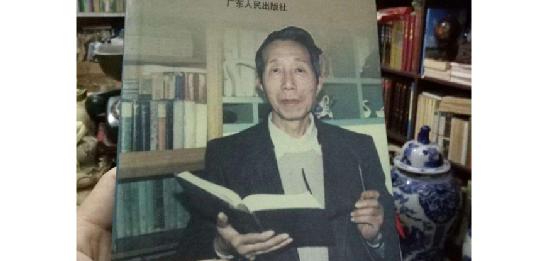
戴镏龄先生(1913—1998)[图片源自网络]
学者小传
戴镏龄先生,汉族,191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早年留学英国,师从莎士比亚研究权威约翰·多佛·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先生,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领域。1939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教授、系主任和校务委员。
戴先生历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比较文学研究会、广东外国文学会顾问,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暨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译林》杂志编委,国际笔会广东中心成员等职。1998年病逝于广州。
戴镏龄先生1939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任教至1953年。在中南五省外语院系合并入中山大学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1954年暑假国家高教部下发经修订的西语系英语专业教学计划,戴先生十分高兴。他深有感触地写了《对西语系英文专业新教学计划的几点体会》一文;他认为,“这个专业教学计划科学体系严密,培养目标明确,使教者学者都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把这个计划与旧大学英语系比较,认为旧大学英语系的课“支离破碎,各不相关,好象是凑起来的一个拼盘”,“中国历史和中国语文受不到丝毫的重视”。而新的教学计划,“每一门课都有其自身的目的和要求,而又和别的课息息相关,不可分割;顾到广阔的基础,也顾到专业的训练。”拿“英国语言学史和普通语言学来说,这是过去西语系很少开设或根本不曾开设过的课程,而在今天的教学计划上却是地位显著,因为对于照顾科学体系和培养研究能力,这都是必要的。”通过新旧对比,他体会尤深,写道:“新的课程也意味着我们的教师必须结合教学在科学研究上作出新的努力,才能担负起为国家培养新的建设人才的任务。”
戴镏龄先生早年就有相当强的科学研究能力。20世纪30年代,即用英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陆续发表论文。在中山大学1954年校庆举行的第一次科学研讨会上,他带头撰写论文参加。10月15日,时称西语系的英语教研组先行举行了第一次小型科学研讨会,戴先生报告其论文《德来登如何建设英国的文学翻译理论》,报告中他“肯定了德来登在建立翻译的正确规则和榜样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着重指出他的符合于今天的翻译标准的地方(如保持祖国语言的纯洁性),同时也指出了他的时代和社会所给他的局限性的缺点。这篇报告给大家的启发很大。”语言学家及翻译家王宗炎先生说这篇报告“用自己的话语写出,简明扼要,是经过了一番消化作用的。”文学家及翻译家顾绶昌先生认为报告中所强调的翻译要“保持原文的风韵”这一点,使他在翻译工作中提高了警惕性。同年11月14日,戴先生便以此篇论文在西方语言文学分组会作了报告,专家学者对这一报告予以高度评价。
戴镏龄先生从教近60年,开设了“英语诗歌”“欧洲古典名著”等10多门课程,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英语语言文学界8位博士生导师之一,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外语专门人才。他教学认真负责,并有创新精神;他在外语系为本科生开课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已在国内首次指导词汇学研究生。例如他的学生、词汇学家伍谦光先生在教学改革方面勇于开拓,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国家教委教学改革评估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和表扬。又如他的学生、比较文学家蔡宗齐先生最近与海内外专家学者联手合作,与时俱进,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创新之举。戴先生被誉为“广东英语教育体系开创人”,为我国英语教育界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他的学生、应用语言学家桂诗春先生是我国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人,并在广州外国语学院(现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办全国第一个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为我国应用语言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贡献。

戴镏龄先生与王宗炎先生(右)和方淑珍先生(左)在研究英语教学问题[图片源自网络]
戴镏龄先生常结合教学,或参加学术讨论、举行科学研讨会,或应有关出版机构之约,撰写论文或翻译论著。其中译著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英/克里斯托夫•马洛著),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英国文学史纲》(苏/阿尼克斯特著),与吴志谦等合译,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乌托邦》(英/托马斯·莫尔著),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上他倾注20多年心血,追求形式美的对衬,堪称一绝,可惜全部毁于“文革”之初;“文革”后,他主编的《英语国家文学名著文库》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83年9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举办建国后首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颁奖大会,《乌托邦》一书获二等奖;戴先生能译出如此经典佳作,与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关系密切。
戴镏龄先生为人低调,做事诚实,淡薄名利。在《我与翻译》一文中,他说:“我30年代初曾翻译过一本书,现在连书名都记不起了,幸亏流传不广,因为我的译文很不成熟。我当时虽也在报纸杂志上用英文发表文章,那完全是少年狂简进取的一股冲力所驱使的,实际上英文修养还很差,至于汉语的运用也是十分生硬。”戴先生还曾写过一篇《戴镏龄小传》,但这篇小传竟然“小”到不足500字,且不少文字只是人生的感言;由此可见,他对名利的淡泊。
戴镏龄先生晚年曾多次中风,即使身体情况每况愈下,但直到临终仍笔耕不辍。他逝世后,其夫人徐开蜀先生遵照其遗愿,把他的手稿及英汉图书4600余册捐给中山大学图书馆,该馆设“戴镏龄教授纪念室”收存;其亲属捐款设立戴镏龄先生助学金,用于资助中山大学贫困生。另外,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也设立戴镏龄先生奖学金,用于奖励中大外院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生。
今年是戴镏龄先生诞辰110周年,特撰这篇小文,谨此纪念。
文/刘兰芳(作者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猜你喜欢
百科04-23
什么是降息?降息意味着什么?百科04-2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百科04-21
蚂蚁庄园今日答案4月21日百科04-19
清朝历代帝王顺序表百科04-19
蚂蚁庄园今日答案4月19日百科04-18
蚂蚁庄园今日答案4月18日